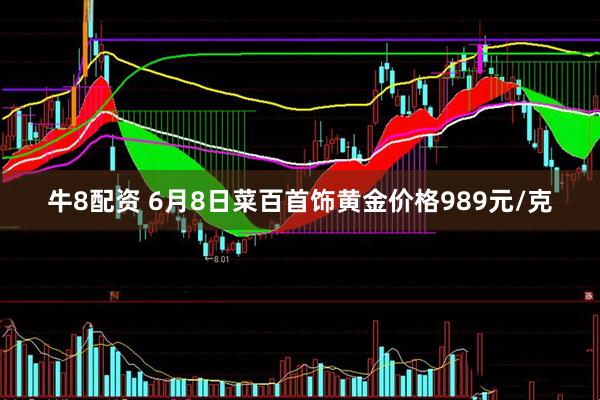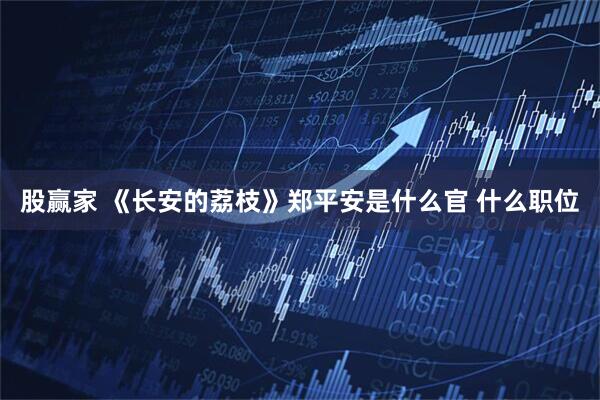海
清晨六点,码头笼罩在一片薄雾中。辽宁省地震局的三名青年技术骨干——钱蕊、安祥宇和孔祥瑞,已经背着宽频带地震仪和网络设备箱在船边等待。这支由辽宁省地震台和科创中心技术骨干组成的队伍,今日将前往海上风电平台开展设备调试工作。辽宁省地震局已多次派出队伍赴风电平台勘选测试,这支队伍只是其中一支。
“海上漂”的苦与乐
海上的工作环境并不轻松。刚过上午8点,刺目的日头已经把海面烤得发颤,天上连一丝云絮都挂不住,毒辣的阳光像泼洒的熔金,直直砸下来。空气里全是被晒透的燥热,每一口呼吸都带着灼意。乘船去海上风电平台的路上,风浪颠簸船身摇晃得厉害,钱蕊打趣道:“我们这叫‘人工过山车’,免费体验,还附赠晕船套餐。”
展开剩余79%科考船停靠在海上风电平台下
装备里的“生存智慧”
出海勘测,装备是关键。海面风浪正猛,船身被浪头掀得上下颠,说话都得扯着嗓子才能压过呼呼的风声;毒辣的日头又像贴在头顶的火球,阳光碎成千万片玻璃碴子往皮肤上扎,裸露的手背晒得发红发烫,连空气都被烤得发黏。
他们的背包里藏着不少“夏日生存法宝”——安祥宇的多功能工具钳最是顶用,风急浪涌时能牢牢拧住松动的设备卡扣,免得仪器被狂风吹得晃悠;钱蕊备的遮阳面罩带了三道防风绳,绳结在下巴勒出红痕也不敢松,不然脸准得被晒脱皮;孔祥瑞的冰感速干毛巾刚浸过海水拧干,贴在脖子上瞬间化成白气,混着汗珠子往下淌。 “你看这风,帽子没绳早吹海里了,”他抹了把额角的汗,盐粒在皮肤上映出白印,“太阳更狠,不搭这冰毛巾,脑门上的汗能直接滴进仪器,录入数据时手滑得按不准键。”
孔祥瑞系好安全绳从科考船爬上海上风电平台
同事们在海上风电平台上调试设备
出差途中的步步惊心
下平台的楼梯比想象中要陡一些,风从梯架间隙钻过来。安祥宇拿着那台有点沉的地震设备往下走,低头看时,只能看到退潮后距离楼梯30多米的海面。“这设备看着不大,压在身上还真有点分量。这高度,手里东西沉一点就发飘。” 他手掌贴着护栏慢慢往下挪,每一步都先让前脚掌踩实了才敢动重心。孔祥瑞拎着仪器紧随其后。
三名同事从海上风电平台下“天梯”
“得快点!退潮了,浪越来越大了!”孔祥瑞拎着另一台仪器跟下来,声音被风撕得碎碎的。他盯着科考船船身的起伏,额角的汗顺着下巴滴在设备外壳上,“这船晃得邪乎,等浪把船推近就跳,慢一步就被拉开了!” 安祥宇深吸口气,瞅准浪头把船推近的刹那,船舷离平台边缘只剩半米,猛地弓身往前冲——脚刚踏上船舷,浪头突然往后拽,船身“哐当”一声退开,他踉跄着往前扑,膝盖重重磕在甲板上,手里的设备却死死搂在怀里。孔祥瑞紧随其后,后脚跟刚蹭到船舷,浪头又猛地掀起来,船身瞬间抬高半尺。他下意识蜷起腿,整个人摔在甲板上滚了半圈,仪器在怀里撞得“咚”一声。两人趴在甲板上回头看,刚才落脚的平台边缘,浪头已经卷着拍上来,要是慢上半秒,脚稍一滑,就得连人带设备坠进那片翻涌的海浪里。
两人趴在甲板上缓了好一会儿,才互相拽着爬起来。安祥宇抹了把脸上的盐粒和汗水,望着渐渐被浪隔开的风电平台,喘着气说:“总算顺利下来了。” 钱蕊把仪器往舱里挪了挪,回头看了眼天边沉下去的日头,“浪越来越大了,先把设备归置好,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明天天一亮,还得再来。”
三名同事回到科考船上
野外地震人最真实的模样
对于地震人来说,每次出门勘测,都是跟老天爷打交道,也是跟自己较劲儿。甲板晃得站不稳,他们就蹲在那儿一笔一画记数据;太阳烤得人后背发烫,手里的设备还得调得丝毫不差。他们总说笑着对付这些难,其实都是把这份活儿的分量揣在心里。
地震人的故事就是这样: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就是一天天在风里浪里守着;不说啥漂亮话,苦的时候递块冰毛巾,累了互相搭把手,这点热乎气儿比啥都实在。可就是这些平常日子里的坚持,透着他们实打实的拼劲儿,这才是辽宁地震人最真实的奋斗底色。
同事们在海上风电平台上调试设备
供稿:融媒体驻辽宁局通讯站 卢山
转自:地震人爱一配
发布于:北京市瑞和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